研究揭示湖泊多营养级群落生态突变中的“同步性密码”
生态系统稳定性是生态学领域长期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学界一直存在争论:物种数量的增加是否一定能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抑或群落间的“同步性”在维持稳定性方面更为关键?在外部干扰或者生态系统状态转变过程中,湖泊多营养级群落的组成与功能发生显著变化,已引起生态学家和管理者的广泛关注。
特别在浅水湖泊中,由大型水生植被主导的清澈状态转变为以浮游植物主导的浑浊状态,不仅破坏了生态系统稳定性,还加剧了藻华爆发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甚至还会将全球湖泊推向超越安全运行边界的风险状态,给生态修复带来巨大挑战。因此,理解湖泊生态系统突变过程中水生群落结构与功能的变化规律,仍是当前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
在这一背景下,生态同步性—即物种或群落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波动是否一致,逐渐成为理解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新视角。同步性增强可能会放大生态系统的波动性并降低其稳定性,而异步的动态则往往通过物种间的补偿效应来提升生态弹性。因此,研究湖泊状态转变过程中多营养级群落同步性变化,不仅有助于揭示湖泊生态系统动力学的内在机制,还能为理解湖泊生态预警与制定科学管理策略提供新的思路。
近期,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张科研究员团队聚焦上述科学问题,选取长江中下游典型浅水湖泊—梁子湖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古湖沼学方法与遥感监测数据,系统揭示了过去百年来该湖多营养级群落的长期演化过程,并基于生态系统同步性视角,解析了湖泊生态状态转变前后水生群落内及群落间同步性动态变化(图1)。

图1.(a)基于多指标古生态时间序列重建湖泊多营养级群落组成变化,使用5年滑动窗口检测物种与群落同步性;(b)物种或群落随时间变化的同步性概念图;(c)湖泊生态系统突变模式(以水生植物为主的清水态,到水生植物与藻类共存,再到以藻类为主的浑浊状态)。
研究发现:
· 过去百年间,梁子湖生态系统经历了两次显著的生态转变,分别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和2010年代中期(图2)。
· 基于沉积藻类色素(pigment)、地球化学指标,以及已有的硅藻亚化石、枝角类和水生植物大化石等古生态记录,并结合遥感数据,揭示梁子湖生态系统在过去百年间经历了三次状态变化。1960年前湖泊以沉水大型水生植物为主的清水态,1960~2010年转变为水生植物与藻类共存状态,2010年后演变为以藻类为主的浑浊状态(图3)。
· 基于同步性理论,揭示了湖泊早期由沉水植物主导,水生植物群落同步性较低,浮游植物数量较少。20世纪60年代后,受筑坝与农业活动影响,湖泊进入过渡阶段,表现为营养盐富集、藻类产量增加以及水生植物向挺水和漂浮型群落转变。同期,藻类群落同步性下降,而水生植物同步性上升,伴随群落稳定性下降。2010年后,湖泊进入藻类主导状态,特征为藻类大量繁殖且低同步性,以及退化水生植物群落的持续高同步性(图4)。
结语与启示:
研究表明,梁子湖的两次重大生态转变均伴随着群落同步性的显著变化。基于此,研究建议在湖泊修复与管理中纳入“同步性视角”,以提升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具体建议包括:
· 恢复不同功能群水生植物(如沉水、挺水及浮叶植物)的共存,可增强功能互补性、降低物种间同步性,并提升整体生态系统稳定性;
· 全面控制外源与内源营养盐输入,防止在高营养胁迫下发生同步崩溃;
· 通过水位调控或生态补水模拟自然扰动,可打断营养级间的同步路径,延缓或阻止藻类主导状态的形成与繁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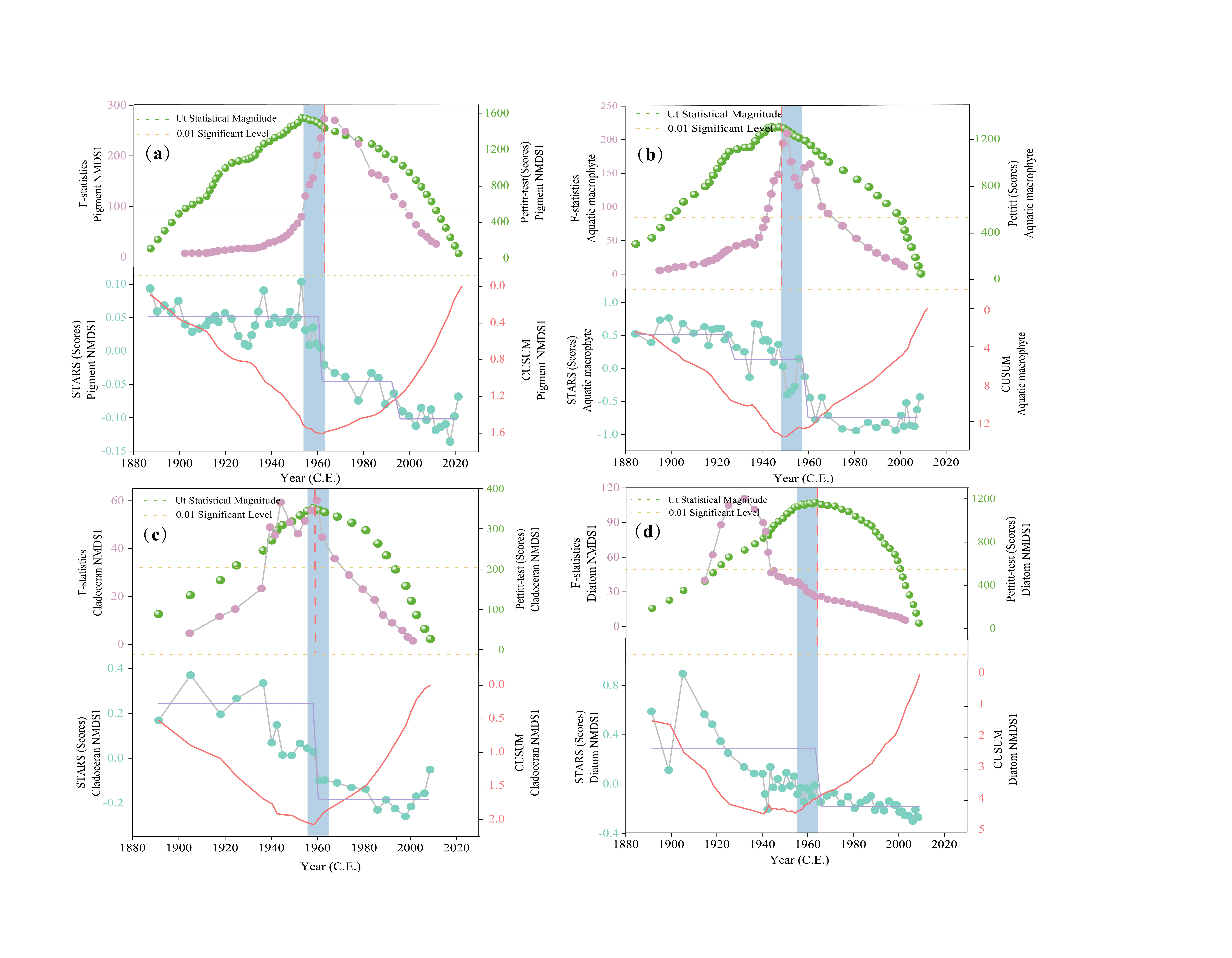
图2. 基于STARS算法、CUSUM检验、Pettitt检验和F检验,对梁子湖重建记录中四类生物群落(藻类、水生植物、硅藻和枝角类)NMDS1进行生态状态转变检测的结果。(a)藻类群落;(b)大型水生植物群落;(c)枝角类浮游动物群落;(d)硅藻群落。

图3. 梁子湖生态系统的三阶段演变模式:(a)阶段I(1880–1960);(b)阶段II(1960–2010);(c)阶段III(2010–2021)

图4. 梁子湖生态系统群落内与群落间同步性的时间动态变化。藻类群落内同步性:(A)1880–2021年,(B)1880–1960年,(C)1960–2010年,(D)2010–2021年;水生植物群落内同步性:(E)1880–2021年,(F)1880–1960年,(G)1960–2010年,(H)2010–2021年;群落间同步性:(I)藻类与枝角类(1880–2010年),(J)水生植物与藻类(1880–2021年),(K)枝角类与水生植物(1880–2010年)
上述研究近期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Water Research上。
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watres.2025.124402

